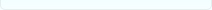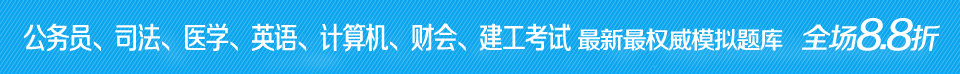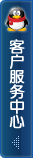當(dāng)前,很多人倡導(dǎo)閱讀,似乎總認(rèn)為“非功利化”的閱讀才叫
閱讀,仿佛這樣的閱讀才達(dá)到了一種境界,才顯得高大上。在這種論調(diào)下,“功利化閱讀”受到輕視,就是難免的了。
個(gè)人以為,我們應(yīng)該正確看待“功利化閱讀”。古人往往用“學(xué)富五車”來(lái)形容誰(shuí)書讀的多,但那時(shí)候書的數(shù)量和種類總共就那么多,他們遠(yuǎn)沒(méi)有面臨像今天這樣的選擇困境。試想一下,當(dāng)我們面對(duì)無(wú)涯的書海,就算終其一生,所能讀的書也只是滄海一粟。在這種情況下,如何選擇就成為必要。
那么,如何選擇呢,無(wú)非是兩種方向:一是自己感興趣的,二是對(duì)自己有用的。而第二種選擇,就難免會(huì)被歸入到“實(shí)用主義”或“功利化閱讀”的范疇。
其實(shí),選擇對(duì)自己有用的書,無(wú)論是為了提升自己的人文素養(yǎng)也好,還是專業(yè)能力也罷,這些都是必須的。而且,功利化閱讀應(yīng)該是一切閱讀的基礎(chǔ)。如果你連那些應(yīng)該讀的、對(duì)自己有用的書都沒(méi)有讀,卻反倒去選擇那些與我們的工作、專業(yè)和生活關(guān)系不大的書,是不是有點(diǎn)本末倒置?
而事實(shí)上,無(wú)論你選擇讀任何書,選擇的過(guò)程就有“功利化”的影子。比如,我最近在看著名作家王宏甲的《無(wú)極之路》。這篇文學(xué)作品發(fā)表于1990年。我起初讀它,是因?yàn)槲艺J(rèn)識(shí)了這個(gè)作家,請(qǐng)他做過(guò)《漢江論道》的嘉賓。我選擇讀這本書,看起來(lái)是“去功利化”的。但這本書為什么吸引我,是因?yàn)闀械闹魅斯珓⑷铡H绻旁诮裉欤瑒⑷胀耆莻€(gè)清廉務(wù)實(shí)的領(lǐng)導(dǎo)干部的典型,可最后他并沒(méi)有得到提拔,甚至一度遭到排擠。但在劉日心中,無(wú)論提拔還是不提拔,都不能阻止他為黨工作,為這個(gè)國(guó)家工作。《無(wú)極之路》還有下部,叫《永不失望》。這本書給我最大的啟示,是無(wú)論環(huán)境怎樣變化,無(wú)論別人如何對(duì)待,我都要做到“永不失望”。那么,我讀這本書,就不僅是因?yàn)楦信d趣,同時(shí)因?yàn)樗鼘?duì)我有用。很多時(shí)候,從書中獲取一種精神的力量,或許比獲得短暫的知識(shí)更為重要。有了這種力量,我們才會(huì)更加堅(jiān)定前行的方向,我們可以在書中獲得成長(zhǎng)。
所以,我們不應(yīng)該簡(jiǎn)單地把讀書分為“功利化”和“非功利化”兩類,這兩者不可能做到那么涇渭分明。過(guò)去,我曾經(jīng)寫過(guò)一篇評(píng)論《有用之書要讀,“無(wú)用”之書也要讀》。事后我曾反思,什么是“有用之書”,什么是“無(wú)用之書”,其實(shí)也都是相對(duì)的。而且,把書分為有用或無(wú)用,本身就是一種功利性的區(qū)分。那么,我們又怎么做到純粹的“非功利化”呢?
來(lái)源:襄陽(yáng)日?qǐng)?bào)
文/蕭雨林